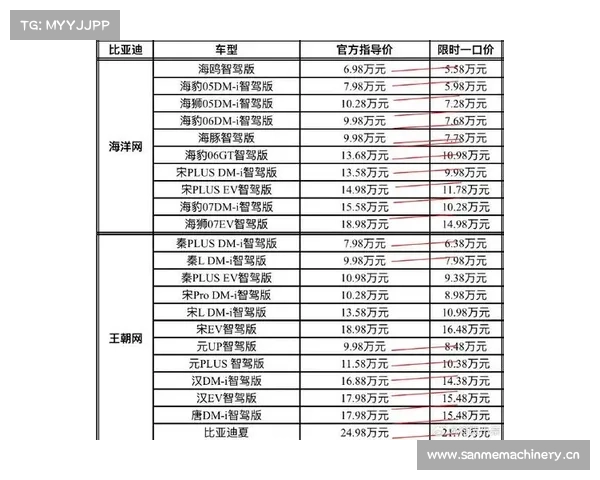“2007年3月2日下午四点,灯光还在调,王朔偏过头问制片人:‘李敖?那老兄顶多算大学老师,他好意思管自己叫大师?’”一句半真半戏谑的话,把现场气氛瞬间点燃,也奠定了那期《凤凰会客厅》“火药味”的基调。
那是王朔离开公众视线整整七年后的正式亮相。他带着新书《我的千岁寒》返京,从机场到凤凰录制间一路被媒体“长枪短炮”包围。尽管多次声称自己“准备收敛”,可坐到镜头前,他依旧锋芒毕露,尤其谈及与自己同属“毒舌俱乐部”的李敖时,更是毫不留情。
说回王朔本人,1958年生于南京军人家庭,却在北京长大,这座城市像一张粗糙的宣纸,早早吸收了他那些乖张想象。高中毕业遇上“上山下乡”尾声,他索性参军当了操舵兵。水兵生涯苦不苦?他在小说里写过:“夜里轮班像跟大海耗赌资,一手好牌也可能被浪翻。”从那段漂浮日子里,他攒下第一批写作素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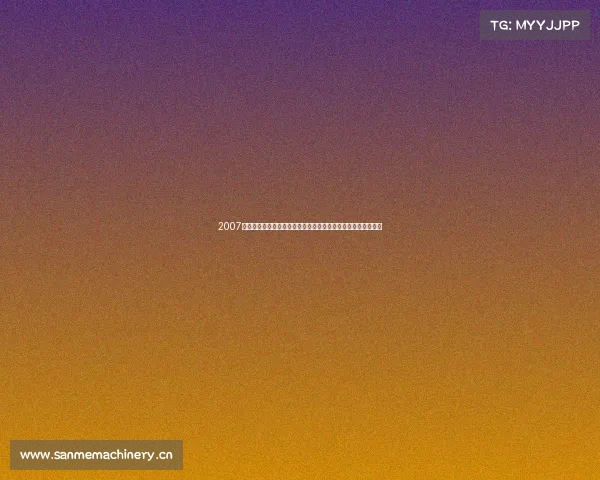

1978年,《等待》悄悄登上《解放军文艺》,里面没有神圣的战役,只有一个北京姑娘和父母的价值冲突。稿费不高,可编辑一句“这小子行”比什么都提气。两年后退伍,他被分到医药公司跑业务。“卖药跟写作一样,都得忽悠,但前者还得懂库存。”王朔自嘲道。三年苦差让他明白:不写字就浑身难受,于是干脆辞职,拉好友开烤鸭店,结果鸭子没烤红火,倒把他写作的劲头彻底烤出来。
1984年,《空中小姐》发表,水兵爱上空姐的新鲜设定让读者眼睛一亮。两年里,他又连掷《一半是火焰,一半是海水》《顽主》两枚重磅。1988年,被戏称为“中国电影王朔年”——《顽主》《一半是海水……》等四部改编片扎堆上映,他戏言自己“横趟”电影界。那一年,有人给他贴上“痞子文学”标签,也有人说他“把北京大院的油滑写成了时代风格”。
影视圈对王朔的迷恋不止电影。1990年,《渴望》掀起全国收视狂潮;《编辑部的故事》一出,情景喜剧在国内有了模板;1994年,《过把瘾》让王志文、江珊爆红。姜文把《动物凶猛》改成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,电影横扫威尼斯与金马,夏雨拿下双料影帝。王朔本人却在热闹高潮后突然收声。
母亲离世、挚友病故,他一度迁往美国,过起躲避采访的生活。直到2007年,《我的千岁寒》杀回书市。伦敦书屋每字3美元购下版权,折合365万人民币的版税刷新当年纪录。接受凤凰专访正是为这本书造势——他自己把它形容为“佛经架子上挂满市井葫芦”。
节目中,主持人请他给当代作家排座次。王朔先摆出“北京队”与“浙江队”的擂台:北京有曹雪芹、老舍再加他,浙江则是鲁迅、金庸配余华。然后他像裁判又像解说:“《红楼梦》对《阿Q正传》,你说能不1:0?老舍有《骆驼祥子》,金庸赢不了。至于我和余华——我这新书一出,2:0,别争。”若换别人说,难免自大;可观众偏爱王朔这种带刺的夸张,因为那股“横”劲儿是多年形成的个人标识。

紧接着话题转到李敖。李敖出生于哈尔滨,在北平度过童年,也爱怼人,两人看似旗鼓相当。可王朔先是语速飙高,一连串短句射出:“三脚猫功夫、坐六年牢就当资本、小家子气!”随后又抛出“大学老师论”:“他敢接‘大师’,我就敢拆。’师’有大小,教书算老师,扛学术再谈大师。”这番说法虽刻薄,却引来不少中年观众拍手,因为他们熟悉李敖的锋利,却也目睹李敖晚年对媒体的“自带把柄”。
比较耐人寻味的是,王朔并不否认两人“同属嘴快的人”。他说:“嘴快没错,错在没料还嘴快。怼人要给证据,要有文气。”这句点评其实隐含了他对自己写作策略的自信:以文本立身,再用快嘴锦上添花。李敖则常以脱口秀见长,学术著作虽多,却多被学界质疑考据粗疏。两人的分歧,本质上是“文本派”与“节目派”的路径差异。
pc28预测顺带提一句,王朔那天也顺势讲了“明星榜”:凤凰台的曾子墨“范儿正”,梁文道“嘴里有货”,何亮亮“报道沉稳”。对年轻观众而言,这些名字或显陌生,但对四五十岁的男性来说,却是熟悉面孔。王朔深知自己受众在哪儿,发言时有意埋梗,既抬高“自家台柱”,也保证了在场观众的参与感。
谈到新作销售策略,他直接劝80后、90后别买:“你们跟父母要钱买,回头怨我骗你们。真想读,等三十岁、家里办过丧事再说。”这句话听上去“嫌钱少”,其实是他拿生死议题垫底的推销套路——把门槛抬高,反而激起一批人想挑战。
王朔也没绕过自我忏悔:“酗酒、抽烟、打群架——坏事我干得不比别人少。可我想往上爬,得给自己编条绳子。”他把“写作”视作那根绳,用语言一寸寸往上攀。有人揶揄他“张狂”,可耐不住作品稳稳立在那儿;有人嘲笑他“老愤青”,可他自己说:“愤青好歹有真火,比装绅士强。”

节目尾声,主持人追问“如何看待敌人”。王朔说,他宁可要锋利的敌人,也不要虚假的赞歌:“敌人像反物质,撞上才能显形。不撞,谁知道你哪儿有毛病?”这话不新鲜,却恰好与当场的“李敖话题”形成首尾呼应——李敖或许正是那个被他视作“必要的反物质”。
透过那期专访,观众看到的是一个依旧张牙舞爪、同时带着中年疲惫的王朔。七年沉寂并未磨平他的棱角,反倒让他学会把棱角打磨成可控的“表演道具”。有人喜欢他的直率,有人厌倦他的自负,但不可否认,他的一开口,总能让话题立刻升温。
至于王朔和李敖孰高孰低,这个问题大概永远难有定论。文学史通常不凭嘴皮定输赢,终归还是看作品能不能经得起时间这把刻刀。不过,当两位“快嘴”同处一个时代,互相吐槽也好,彼此借力也罢,至少为华语世界贡献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公共言论秀。和任何文坛纷争一样,热闹过后还得回到写作本身——别管他自称“北京代表队”,或如何讥讽“东北出身的大师”,读者手里的那本书才是分高下的最后裁判。